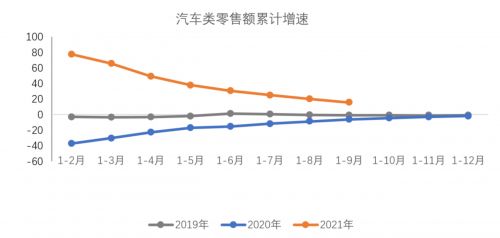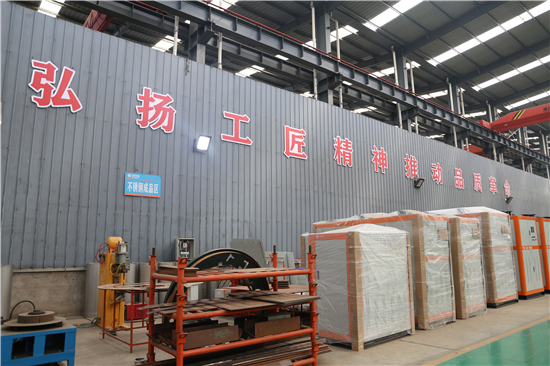“当我没有关注互联网时,我的吸引力就指向了那些散落一地的兴趣爱好。它们已经在那很久了,现在突然冒出来,就像蒙了灰后一下子擦亮。”24岁的孟褚荔在远离互联网的过程中,重拾爱好。
在豆瓣“反技术依赖小组”里,有超过两万名组员,他们聚集在这里,目的是“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造成自己某些能力的退化”。
相应的,还有“远离屏幕计划”小组,成员数量超过3万;在“数字极简主义者”小组,超过18000名组员,一同尝试合理使用科技,“找到自己真正认为有价值的事”。
在这些小组中,有人尝试远离智能手机,改用按键式小屏幕的“老人机”;有人放弃电子支付,通过现金恢复消费的掌控感;还有人建群互相监督,每日互发手机使用时长。
在我们的采访中,26岁的李蓝决心远离互联网是因为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:时间似乎不多了,虽然才二十六七岁,但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。她不希望到老的时候,发现时间都花在刷手机上。
她卸载了最常使用的APP,改用网页版登陆微博和豆瓣。为了增加使用社交网络的“目的性”,她将闪念记录在纸上,集中搜索。她发现,许多临时起意的点子,不搜也没关系。
对她来说,更关键的是找到互联网之外的乐趣。比如,和朋友沉浸式聊天,和陌生人偶然对话。她感受到,在网络世界真真切切地思念一个人有多可贵。
28岁的小小星是新闻传播学博士在读,更多的时候,她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活跃在这些小组,关注人们远离互联网的种种尝试和感受。
在小组里,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:一群为了远离互联网的试验者们,聚集在互联网上寻找办法和鼓励:他们本身是要脱离互联网,但是由于要脱离,又不得不在互联网上寻找社会支持。
【1】李蓝,小学语文老师
“时间似乎不多了,通过手机获得的快乐,好像无法让我在老年问心无愧”
上大学时,李蓝会周期性地觉得,自己刷社交软件刷得太多了。她喜欢看视频网站的推荐视频,或是根据一个帖子顺藤摸瓜,四处搜索浏览。越看越睡不着,一下就到了凌晨两三点。
渐渐地,她发现这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影响。最大的感受是,她的注意力不再像之前一样集中了。
她无法沉浸地看完一部两小时的电影。看书十几分钟,她就自然拿起身边的手机。
社交也受到了影响。和朋友交流时,她即便还在讲着话,也会习惯性地拿起手机,看有没有新消息。
李蓝说,她甚至有种强迫症,睡前必须把社交软件过一遍,确定没有任何一条需要回复的消息之后,“好,我可以睡了。”
直到最近,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:时间似乎不多了。
“通过手机获得的快乐,好像无法让我在老年问心无愧地说,‘我年轻的时间没有浪费’。”李蓝说。
她先将使用时长最高的两个软件卸载:微博和豆瓣。她曾经一天花两三个小时在微博上,“到了周末,更是住在微博”。
现在,她改用网页版,只浏览关注列表的信息,使用时长大大降低。
她开始增加社交网络使用的“目的性”:如果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搜索的念头,先记在纸上,累积几个后集中搜索,减少无意识的搜索和浏览。她发现,其中许多都是临时起意的点子,不搜也没关系。
李蓝的搜索备忘录。采访者提供
更重要的是,她要发掘更多的爱好,填充不玩手机的时刻。
她开始学韩舞,“以前总觉得自己跳舞就像跳广播体操”,现在她仍然对自己的舞技不算满意,但每一次练舞,她都收获了极大的快乐。“在一个小时里,和十几个同学一起,非常专注地跟着老师学习,这种感觉特别好”。在舞蹈室,她面对镜子,“营造出一种‘姐很拽’的气场”,“整个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。”李蓝说。
在舞蹈室里,李蓝还意外遇到了同事,二人的话题慢慢变多。一个周五的夜晚,李蓝和她吃完饭,一路走到钱塘江边。她们聊得非常开心,在那一个多小时里,一次都没有拿出手机,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纪念照片。
同事比李蓝小两岁,最近也产生了远离互联网的念头。她曾经总是点外卖,吃完看看手机,时间哗地一下就过去了。她决心慢下来,选择了做饭的方式,“让时光被自己感知。”
和同事的这次聊天后,她惊喜地发现,对方和她之前所认识的大不相同。以前她们也常一群人约饭,对方只是嘻嘻哈哈的。
前段时间,大学同学发给她一篇书评,二人由此聊开来,但她更希望面对面和对方聊一聊。“那种沉浸在我和她的小世界的感觉真的很好。”
“在这个网络世界里,如果你真正在思念一个人,不是突然想起了这个人,这是非常珍贵的。”李蓝说。
【2】孟褚荔,法律行业
“当我没有关注互联网时,那些散落一地的爱好突然冒出来,就像蒙了灰后一下子擦亮”
孟褚荔是个很在意准点下班的女孩。约定的采访时间原本是傍晚6点左右,想了一会后,她说,“五点半吧,别耽误你们下班。换位思考,让我多加一分钟班我也不高兴。”
今年是孟褚荔工作的第三年。从学生到职场人士的身份转变,让她的生活和心态发生了很多变化。工作中,她不得不使用手机,还需要下载办公软件钉钉,为了应付随时到来的加班指令,“很讨厌”。
工作之后,玩手机对她来说成了一种内耗。孟褚荔说,“它占据了我下班后的太多时间,让我觉得一天就这样过去了,什么都没做。”
多的时候,一天中她能有十三四个小时花在手机上。她喜欢侧躺在床上看网络小说,“像虾一样蜷着”,能从下午六点看到凌晨两三点。看到忘记时间,偶尔腾出一只手拿零食往嘴里喂。
时间久了,她也觉得没意思。除了网络小说,整个网络环境都让她感到无趣,那里充斥着骂战和攻击,商业化气息也越来越浓。她从内心产生抗拒的欲望。
现在,她喜欢把手机放在卧室,喊几个朋友一起在客厅拼图、画画,一玩就是几个小时,“根本想不起来打开手机”。天气好的时候,她会和朋友一起到公园散步、聊天。
因手机而退化的感受力恢复了:她好奇地关注一切,观察路边的行人,被欢快奔跑的猫狗治愈。
孟褚荔的拼图作品。采访者提供
24岁的孟褚荔与互联网的接触有一个有趣的弧线。
她上网很早,2010年左右,她刚上初中,还用着MP4,网上最火的是贴吧,她在这里爱上了橡皮章、十字绣等各类手工。2014年前后,知乎向公众开放注册,收获众多用户,孟褚荔受其引导,参加了不少活动、大赛,积累获奖经历。“小红书引发我的消费主义,豆瓣又将我引向极简”,之后,她爱上了登山、徒步、旅游。
孟褚荔历数自己的爱好,拼图、绘画、篆刻、橡皮章……她最近还在尝试体验流体画和滑冰。“当我没有关注互联网时,我的吸引力就指向了那些被我散落一地的兴趣爱好。它们已经在那很久了,现在突然冒出来,就像蒙了灰后一下子擦亮。”
但她承认,控制力时起时伏。如果当天的工作内容有趣,她就能积极地发掘自己各种爱好。如果这一天上班什么都没做,她的心情会变得糟糕,玩手机的时间也陡然上升。
孟褚荔的橡皮章。采访者提供
【3】夏星,新闻传播学博士在读
“你本身是要脱离互联网,但由于脱离,又不得不在互联网上寻找社会支持。”
夏星加入了3个类似“反技术依赖”的小组,发了至少7篇帖子。
她分享过自己关掉微信朋友圈一周的体验,对于媒介化城市的各种思考,甚至包括她在如厕时的技术依赖。
28岁的她是新闻传播学的在读博士,她加入这些小组的初衷并不是利用它作为监督自己远离手机的工具,而是为了她的研究论文。
从一开始,她就以观察者的身份,进入远离互联网尝试者的群体。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:“你本身是要脱离互联网,但是由于要脱离,你不得不在互联网上寻找社会支持。”
夏星说,她本身对于互联网并没有太深的依赖,因为她“对其他人就不是那么关心。”
她曾两次关闭微信朋友圈。一次是考博士期间,她关闭了朋友圈入口。一次是今年1月,她取消了朋友圈更新的提示红点。她发现,仅仅如此,就足够让她失去浏览朋友圈的欲望。“它就像是一种强迫症。”
关闭朋友圈之后,夏星觉得,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偶尔会有一些尴尬的时刻,比如她偶然问起一个朋友何时结婚,随即发现,对方几天前刚在朋友圈分享了结婚证的照片。
另一个让她困扰的是,她关注的公众号太多了。五百个,她根本看不完。她一天最多只会点击十几篇比较感兴趣的推送,其中能认真读完全文的,不过两三篇。
为此,她特意在豆瓣“数字极简主义者”小组里发帖,询问“如何清理公众号”。有人建议她取关所有公众号,再重新搜索她真正需要的。她觉得这个建议不错,但重申自己关注的五百个公众号,她发现自己一个都无法取关。“有一种心理是,你知道你自己看不完,但你又害怕错过。”最终,她放弃了清理。
即使自认为不是互联网重度依赖者,夏星仍能感觉到互联网带给她过多的负面影响:信息疲劳,媒介技术侵犯个人隐私,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挤压,等等。这些影响可以作用到所有互联网使用者,只是多与少的差异。
她的眼镜度数从高中到现在涨了三四百度,“不是因为学习,是因为玩手机,窝在床上看电影什么的。”她的肩颈也时常感到酸痛,需要不时拉伸。感受能力似乎也变弱了,她在网上和人聊得热火朝天,见了面反而尴尬。
3月初,夏星去看了一个名为“回到未来”的展览。三层中有两层是关于智能生活,例如智能家具、智能通讯等。“我觉得很困惑,真的要这么智能吗?”
夏星说,她也不知道未来应该是怎样,只是觉得,大家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不是过于单一了。“一定是一个手机控制全家吗?似乎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”
她希望,未来不应只是万物互联的实现,哪怕是田园生活,隐居,或是其他生活状态都可以的。“未来应该有更多可能性。”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本文中李蓝、孟褚荔、小小星均为化名)
九派新闻记者 王佳箐
关键词: 逃离互联网的一次尝试卸载常用APP